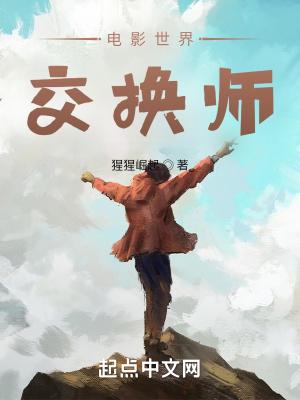倚天中文网>好锦织时节种田 > 9樱桃二(第2页)
9樱桃二(第2页)
他瞥了眼李家吉,粗声骂:“每天满脑子没点正事,竟胡想八想!”
李家吉被骂得一缩脖子,怂了,没敢再提樱桃的事。
八月至,交白露,农家抢收,田里各家都忙得不可开交。
李家要收豆种麦,孙家抢摘棉铃。男女孩们都扛起农具下了田里,李瑜也搁置了几日给孙三娘嫁衣的收尾工作,转而到田里帮忙撒种去了。
天儿终于彻底凉了下来,每日早晨爬起床,李瑜都觉得凉得有些发颤,反倒是田里干活出出汗还能好受些,起码没有夏日那般痛苦了。
这一忙就忙到了中秋节,因今年夏秋两季,李家都收获颇丰,赵氏难得奢侈一把,拿了家里半袋面,去村子里的屠户家换了猪肉回来,给一家人改善伙食,做了顿丰盛的中秋晚膳。李瑜这阵子也在田下忙,所以被分到了两块糖油浸过的猪肉,裹着白面馍馍咬进嘴里,她曾经觉得油腻、高“gi”、不干净的肥肉,如今是这般美味痛快。她吃得肚皮溜圆,内心极其满足,望着高悬的圆月,难得没生出那种强烈的、思念从前的感受。
恍惚间,李瑜竟觉得这日子好像还不错?
过了中秋节便到了秋分,农忙缓了下来,李瑜脱手回家,专心致志地给孙三娘的嫁衣收尾。
其实她对进度一直有控制,心中有数,并不着急。反而是孙大伯娘去摘棉时,常见李瑜在田里帮农,估摸着女儿婚期在即,她却还没见到完整嫁衣的模样,终于有些按捺不住,委婉地找了趟赵氏,催了两句。赵氏趁晚晌与丈夫说了几句,叫把李瑜换回家里来。
毕竟一家人都吃了孙家给的甜樱桃,纵那滋味已模糊,李老爹依旧记得吃人嘴软,便痛快地答应了。
家里的活计赵氏尽量都派给了小儿子,也给李瑜施压,“定要为人家好好做,可不敢拖沓。眼瞅着就要嫁了,嫁衣还没让人家上过身,这哪成啊?”
李瑜为宽赵氏的心,特地抱了裙子到堂屋来给赵氏看,“其实已成型了,就差收边,不日便能让三娘试上。”
赵氏一看那裙子的形制,登时有些惊了,“这是……”
她见那裙子四面裙门,层层叠叠还打了齐褶晃在眼前。赵氏只在县城里的烧香从偶遇的贵妇身上见过,一时连如何描述都不会。
李瑜只能把后世定义的名字告给赵氏,“是马面裙。”
她读书时学戏服,原想过回国能给影视剧做设计,所以还特地研究过一段时间的古装剧和汉服。这本是她读书时候的兴趣爱好,偶尔也在设计作业里增添一些东方元素,实没想到如今能派上用场。
之所以拖了些时日,还是为了将裙面的褶线压实一些。没有电熨斗的日子,折痕就靠物理重量压法了。
赵氏啧啧赞叹,却怕手会弄脏布料,连碰一下都不敢,欣赏了一会便催李瑜快些做好,拿给孙家人开开眼。赵氏已忘了当初如何惴惴,只剩下满心骄傲,自家闺女,竟有如此本事!徒手做出了大户人家贵妇才穿的裙子!
她虽不知做法,但一看就知道这样打过褶极费布料。倒幸亏孙家舍得,不然她闺女徒有这般手艺也没处使。
李瑜完工那日赶巧正是秋社,社日是一年两度的大日子,田沟村的男丁们一早就在保长的组织下去了土地庙拜土地公,祭了牲口,中午则在土地庙外头开了席面,村子里各家的媳妇都帮忙做了菜送来,一时间热闹非凡。今年年景好,家家户户收成俱是不赖,因此菜席整治得极丰盛,凡是嫁了人的媳妇几乎都带了孩子来凑热闹,为着能尝点鲜。
外头敲锣打鼓喜气洋洋,李瑜却没去玩,独个在家,趁清净,正好将喜服收了工。
待席散了,男人们领着孩子归家各歇午觉,村子的舞台便让给了女人们。掌家主妇们算计出之后过冬家人要用的口粮,便开始东西串起了门,把各家种的不同谷物粮食换一换,也好丰富口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