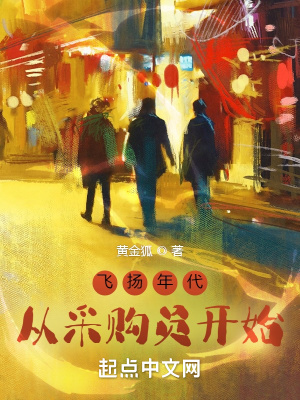倚天中文网>窃玉生香 > 第十七章(第1页)
第十七章(第1页)
容玉不作他想,走近他,借着烛灯凑近了看。李稷倏地抬起头来,一刹间,彼此鼻尖相对。
容玉唰然红了脸,怔忪中,但见他眉目含笑,唇角漾出两个梨涡:“有劳夫人挂心,我没事了。”
因离得近,他声音格外轻,也格外喑哑,猫爪似的挠在耳尖上。容玉心旌一滞,耳鬓蓦地更热,退开一步,道:“下次若有苦衷,与我直言便是,不要再像今日这般。”
李稷的目光从她酡红的面庞上移开,手指落空,莫名觉得痒,忍不住摩挲了下,才道:“是。”
容玉调整气息,道:“今日你为荣王解忧,实也是替我还恩,多谢了。”
李稷道:“你我夫妻,不必言谢。”
容玉一怔。
李稷笑着补充:“我的意思是,我既替子初照顾你,便理应为你做这些,你不必有负担。”
容玉汗颜,念及表兄,蓦感悲怆。时局动荡,天高路远,也不知他现在如何了。这一劫,虽是父亲被舅父连累,但若无表兄与李稷的帮扶,容家断不能安然无恙。
细想来,其实李稷尽管贪玩,待她却是有求必应,慷慨大方。容玉回顾近日种种,越发坚定报恩的念头,看向李稷面前的稿纸,饶是再迟钝,也看得出来那情状甚是可怜。
“这篇策论是因何事而作?行文至此,顺利否?”
李稷听她问起功课,不免捉襟见肘,原想遮掩两句,但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,何况在自家夫人面前露短,也谈不上丢脸,便苦笑道:“议海禁旧制与沿海倭寇之乱。不太顺利。”
容玉自小跟在容岐身后,多年耳濡目染,对策论之法颇有心得,可惜于海禁、倭寇却是一知半解,眼看帮不上什么忙,便道:“上次回府为兄长庆生,他似乎正在看海禁之事,想来也在做这类文章。既然目前写不顺利,不妨先歇一歇,待改日有机会,再与兄长一道钻研。”
其实,她并不知容岐究竟在复习什么,只是想他惯来博闻强识,这类考题于他而言不在话下,这般措辞,主要是想给李稷递个台阶。当然,若是他能听进去,生出向容岐请教的心,则是更好了。
李稷果然眼睛一亮,道:“也是,我竟忘了家里还有兄长这位文昌星君。只是大考在即,他想必也是日不暇给,若是向他讨教,还得仰仗夫人费心。”
“那有何难?明儿我便叫青穗递个信去。你功底不差,资质又好,想来听他提点两句,便也豁然开朗了。”
容玉听他有意向容岐请教,倍感欣慰,夸他的话脱口而出。李稷差点以为听错,待回过味来,嘴角已快咧到了耳边。
容玉看他笑成这样,后知后觉地垂了眼皮,重新取了膳食出来,道:“先吃饭吧。”
李稷抱着手臂,头一歪,盯着她:“夫人刚刚是在夸我?”
容玉目光凝在菜肴上,只道:“吃饭。”
李稷逗她:“夫人夸的是我,怎的自个害起羞来了?”
容玉脸颊热得像被火烧,放完玉箸,嗔他一眼,拿起提盒走了。
*
春闱迫在眉睫,容玉办事又是个麻利的,次日一早,便差了青穗送信回容府,延请容岐来府上小坐半日。
谁知青穗回来,竟告知容岐不在府内,盖因前几日山东老家有一批举子入京赶考,借宿于城外崇光寺,其中一位恰是容岐故友。容岐向来重情,为与友人叙旧,便也搬去了崇光寺,准备与友人同住到大考前。
容玉听得这消息,自是失落,倒是青穗提醒:“姑娘,何不也把姑爷送到崇光寺去?那儿有大少爷看着不说,还有诸多同年相伴备考,读书风气必然极好。更要紧的是,那地方偏远僻静,姑爷若是去了,便没什么机会再偷溜出去寻欢作乐了。”
容玉心头一动,下月初九开考,掰着手指算算,用来复习的日子仅剩二十多天。李稷虽然已作出承诺,保证以后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读书,可就目前而言,他缺的不仅是勤奋与自律,更是他人的指点。
拿定主意后,容玉当天便与李稷提了此事。
李稷才背完一篇《中庸》与她听,原是等她夸奖,没承想等来这样的消息,怔了一瞬,才道:“我背书背得不好吗?”
容玉说“没有”,李稷更想不明白,皱了眉头:“那为何要送我走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