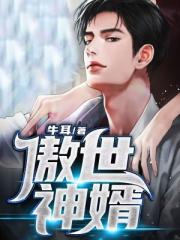倚天中文网>四合院一人纵横 列表 > 第2261章 凤翔于天6(第2页)
第2261章 凤翔于天6(第2页)
李老先生笑着拉起他的手和旁边女孩的手:"你看,两个人互相扶着,才站得稳。就像白先生扶着你阿爷种稻子,你阿爷帮白先生找矿石。"
孩子们似懂非懂,却都认真地跟着念。阿依莎挤到前排,看到地上的"水"字,忽然指着不远处的灌溉渠:"先生,这个字像阿蛮哥哥的水渠!"
李老先生大笑:"正是!白先生说,汉字是从天地万物里来的,你们看这田字,是不是像你们家的耕地?"
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,纷纷捡起树枝在地上画,西域的孩童画得歪歪扭扭,却都带着一股认真劲儿。李老先生看着这一幕,对身边的哈米德道:"白先生当年说,教书要先教孩子们看得见的东西,果然没错。"
佛窟的第五层刚完成最后的彩绘,画师们正在用金粉勾勒壁画边缘。壁画上,粟特商队带着孩童穿越沙漠,中原的郎中在给西域的老人诊病,鲜卑的骑兵在帮农夫驱赶狼群,最显眼的位置留着一片丈许见方的空白,旁边用汉、粟特两种文字写着:"待长安的孩童来此,补画江南的春天。"
念安站在空白处,望着下方的人群。阿蛮正蹲在学堂旁,教中原儒生辨认西域的草药,他手里拿着的《本草纲目》是范宁手抄的,书页间夹着疏勒的稻叶与龟兹的花瓣;佛图澄的弟子与儒生坐在石阶上,争论着"慈悲"与"仁爱"的异同,旁边一个西域铁匠正用中原的淬火法打制农具,火星溅到他们的衣袍上,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。
"将军,范先生的书信。"亲兵递上竹简,上面的字迹清隽,是范宁的手笔:"长安的孩童已选出二十人,带着活字印刷的字模和新培育的桑树苗启程了。他们说要在龟兹种桑树,教西域的姐姐们养蚕缫丝。"
念安将竹简递给身边的李老先生,老先生看完笑道:"白先生当年在江南种桑时就说,桑叶能养蚕,蚕能吐丝,丝能做衣,一件事连着另一件事,环环相扣才是生机。"
画师们围过来,请念安为空白处题字。念安接过笔,却没有写,只是指着下方的孩子们:"让他们来吧。"
阿依莎第一个跑上前,踮着脚在空白处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麦芽糖,旁边用刚学会的汉字写"甜"。其他孩子纷纷效仿,中原的孩童画了江南的乌篷船,西域的男孩画了沙漠的骆驼,鲜卑的女孩画了草原的狼崽,最后竟凑成了一幅热闹的画卷。
画师们相视一笑,提笔在孩子们的涂鸦旁添上背景:麦芽糖的糖纸飘向江南的稻田,乌篷船的帆上画着西域的花纹,骆驼的铃铛连着鲜卑的马鞍,狼崽的脖子上系着中原的红绳。
夕阳西下时,念安站在佛窟顶层,望着远处的商队缓缓进入龟兹城门。商队里有中原的丝绸商,有西域的玉石贩,有鲜卑的皮毛客,他们牵着马,说着混杂的语言,却彼此熟稔地打招呼,交换着路上的见闻。
"将军,北魏的使者来了,说拓跋嗣想派工匠来学习龟兹的彩绘技艺。"周楚走上前来,手里拿着一封密封的书信。
念安接过书信,信封上盖着北魏的狼纹印,旁边却贴着半朵忍冬花,与她护心镜上的图案恰好吻合。"告诉使者,欢迎他们来。"她顿了顿,补充道,"让阿蛮准备新的稻种,作为回礼送给拓跋嗣。"
周楚应声而去,念安的目光却投向了葱岭的方向。那里的云层渐渐散去,露出后面连绵的雪山,山脚下隐约传来驼铃声,越来越近,带着江南的水汽与中原的墨香,正向着龟兹的佛窟而来。
她知道,那些来自长安的孩童会带来新的故事——他们会教西域的孩子唱江南的童谣,会学着用西域的颜料画雪山,会和鲜卑的小伙伴一起在石窟前放风筝。而佛窟的空白处,永远会留着新的位置,等待着更多的人来填补,就像这流动的时光,永远没有终点,却永远在生长。
驼铃声越来越清晰,夹杂着孩童的笑声,穿透佛窟的回响,向着更遥远的西域而去。念安的身影立在夕阳中,护心镜上的忍冬花与壁画上的图案交相辉映,在石窟的岩壁上投下长长的影子,仿佛在说:路还长,我们慢慢走。
龟兹佛窟的晨钟刚落,阿依莎就被一阵清脆的鸟鸣惊醒。她揉着眼睛爬起来,看到窗台上落着一只羽毛翠绿的鹦鹉,爪子上系着个小竹筒。女孩踮着脚取下竹筒,里面是卷桑皮纸,上面用汉文写着:“长安孩童已过葱岭,带桑苗三十株,活字模百个,盼与西域小伙伴共画江南春。”
字迹歪歪扭扭,像是孩童所书。阿依莎虽认不全字,却认得末尾那个小小的忍冬花印章——那是她在疏勒时,阿蛮教她画的第一个图案。她抱着竹筒跑出门,正撞见哈米德在给驼队装水,连忙举着纸喊:“爷爷,长安的哥哥姐姐要来了!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