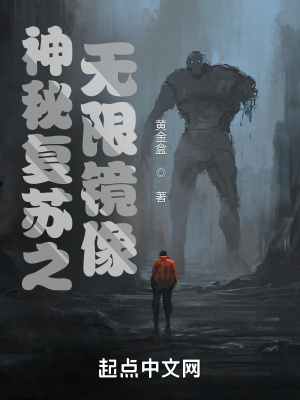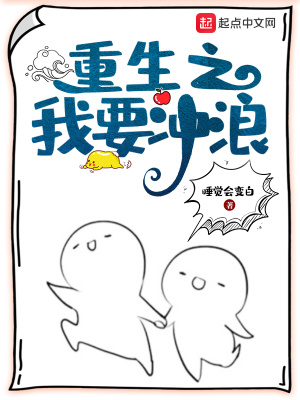倚天中文网>庶子无为(科举)笔趣阁 > 第36章(第4页)
第36章(第4页)
整个茶楼内,刚刚的热闹恭喜声顿时一静,所有人都看向了那名少年。
少年大约十五六岁的年纪,长得浓眉大眼、器宇不凡,一身儒生棉袍,虽不华贵,但也针脚细密、不见补丁,举手投足间一股书卷气,只是说出来的话却很有几分刻薄之意。
沈江云一眼便认出了对方是谁,闻言想都没想,直接对嘲了回去:“怎么?忍到现在才下场,结果还是被我二弟压着没取得案首,心中不服气了?”
沈江霖不认识此人,沈江云却是认识。
两人年岁相当,都在京城中行走,各种宴会雅集上总有碰面的时候,沈江云见过几次此人,他乃是翰林院从七品陶检讨之子,陶临九。
只是陶临九与他根本不是一路人,人家是清贵翰林之子,而他是勋贵侯爵之子,两人的圈子不同,从来没有相谈过。
但是没相谈过,不代表沈江云不知道他。
他的老师秦勉之兄秦之况便是翰林院侍读学士,是陶检讨的顶头上司,秦先生曾言,陶检讨之子陶临九,与他一般大年纪,但是文采斐然,颇有先贤遗风,之所以前面没有和他们一起参加科考,便是想夯实学识后一飞冲天,恐怕意在小三元。
结果压了这么些年,头一回考,居然还被他二弟压了一头,估计此人是咽不下这口气吧?
沈江云虽是猜测,但也猜的八九不离十。
陶临九比沈江霖他们先一步知道自己的名次,原本他这次信心满满能夺魁,谁知道小厮报回来的成绩只有第二名,陶临九当即就沉下了脸。
小厮亦是苦着脸,人家只要中了便欢欣鼓舞,可是他家少爷听到第二名还不高兴。
陶临九心中不舒坦,也没心思问谁得了第一名,正准备结账回去了,却听到了知节高喊的“案首”之声,忍不住扭过头去看,却愕然发现,对方只是一个比他还小几岁的小孩儿。
陶临九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!
再一看,那小孩儿身边坐的是沈江云,从两人有几分相似的眉眼,不难猜出两者的关系,顿时更加的不信。
就沈家这样的勋贵门第,还能教的出一个案首?简直就是可笑!
陶临九瞬间就想到了其他的一些可能性,忍不住就出言讥讽出口。
听到沈江云得了便宜还在那边卖乖,陶临九更是不爽至极,本就绷着的脸,此刻黑沉地要滴出水来,双目之中也满是讥诮:“别人十年寒窗苦读,抵不上你们沈家人读个四五年就能上场拿案首,果然是豪门世家,失敬失敬!”
陶临九朝着沈江霖的方向拱了拱手,想到自己五岁开始进学,足足熬了十年才初入场,想着一举拿下小三元,扬一扬名声,如今面对现在的结果,实在让他够心寒。
他的父亲就是农家考出来的,考中进士后又考庶吉士,入选翰林院,混了多年成了翰林院从七品检讨,因为没有家族根基也瞧不上朝堂上的那些弄权者,他爹一直坚守本心,不同流合污,做着一个穷翰林,将毕生所学和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,如今他却要让父亲失望了。
陶临九心中愤懑失望,如何熬得住不宣泄出口?
沈江云并不擅长与人争执,闻言气的跳脚,却不知道该如何回敬能戳他痛处,还没等他想好,便听他二弟站出来道:“自古英雄不问出处,有才不在年高。若是要以年纪排资论辈,恐怕你也不该得第二名,否则让那些考到头发花白都没考上的老者情何以堪?往后朝廷是否也不用开科取士了,直接以年纪取士便是?”
沈江霖刚刚已经隐隐从旁人的口中知道这便是此次县试的第二名,一个名次的差距,可是天差地别的待遇,难怪怨念这么大。
案首是有特殊的意义的。
京城之中县试、府试是一块的,都在顺天府衙门举行,监考官也都是谢识玄一人,也便是说,既然谢府尹点了他为县案首,那么一般来说除非沈江霖不去考,或者出现重大失误,一个府案首已经算是板上钉钉了。
拿到了县案首和府案首,等到了院试的时候,阅卷官自然会对谢府尹推举出来的案首另眼相看一番,除非两人之间是不死不休的政敌,否则都会给个面子,一个秀才功名是稳的。
这不仅仅是一个名次的差别,关系着后头的诸多利益牵扯,如何不让陶临九在意?
沈江霖身后站在一排同仇敌忾的少年,俱都不服输地盯着陶临九,沈万吉甚至暗戳戳的想,要是这个小子还在这里满嘴喷粪,等会儿就叫兄弟几个人找个没人的胡同,给他套上麻袋教训一顿!